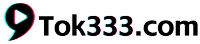责任编辑: mormonconverts.com
世界上首个兼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公民身份的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在1999年与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共同组建了“西东合集乐团”(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邀请巴以两国的年轻乐手到德国开展合作。对于该乐团,萨义德当时说:不是要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要向大众呈现一个“游离于政治联想的隐喻”。
以《东方主义》为代表作的萨义德在几年后离世,但“西东合集”在25年里的“熔炉实验”从未中断。巴以冲突烽火再起的今日,去年底因病已辞任柏林国家歌剧院总监一职的巴伦博伊姆,再度率领西东合集乐团登台伦敦逍遥音乐节(BBC Proms)。
82岁的巴伦博伊姆由61岁的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搀扶着,举步维艰地走上台,坐到指挥台上。身体明显瘦削的指挥家在整晚的背谱演出中,并不见过去的能量和冲劲。选择的两部作品均来自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和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伟大”》。巴伦博伊姆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静止状态,左手偶尔挥舞,惟独双眼仍旧锐利,来回扫射乐团每个角落。
此前,我曾两度与巴伦博伊姆交谈。第一次是2008年指挥家首次访问中国期间,第二次是2015年在伦敦。那年,指挥家曾打算带柏林国家歌剧院乐团到德黑兰演出,却因拥有以色列国籍而在海关遭拒入境。这位阿根廷裔的音乐家告诉我,面对棘手的海关问题,他通常会先说:“我是巴勒斯坦人”,接着再说“可我也是以色列人”,希望利用自己是首个巴以双重公民的事实,去说明两者相融的可能性。
但这个角色也曾频繁给巴伦博伊姆带来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两边不讨好的麻烦事。他否认自己是政治人物,但他多次率乐团登台加沙,以和平的名义举办音乐会,并常做“非政客演说”。由于他多次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侵犯,以色列政府也表示对他“不喜欢”,理由是老巴“利用文化作为宣扬他反以色列国观点的政治平台”。
在形成“和平斗士”的形象之前,巴伦博伊姆的前半生与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有过一段闻名于世的“金童玉女”岁月。上世纪六十年代,巴伦博伊姆在华裔钢琴家傅聪的伦敦家里,与大提琴“天才少女”杜普蕾相识,旋即搭档频繁出现于欧洲和国际舞台,并很快成婚。两人琴瑟和鸣的光彩,一度被欧洲乐评视为“当代舒曼与克拉拉”。然而杜普蕾突患绝症的悲剧改变了两个人的生命轨迹。
1998年,一部以杜普蕾的人生为蓝本的电影《她比烟花寂寞》(Hilary and Jackie)横空出世,当中涉及到巴伦博伊姆与杜普蕾情史的拍得叫座却不叫好。1999年,包括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内的多位具国际影响力的音乐家联名写信刊登于英国《泰晤士报》上,抗议该片“歪曲现实”,巴伦博伊姆还愤然道:“他们就不能等我死了(再拍)吗?”
这段经历和事件已经淡出大众记忆。进入21世纪后,巴伦博伊姆持续活跃于音乐与社会政治之间。比如说,在巴以的又一次冲突不久后举行的200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尾声,指挥台上的巴伦博伊姆转过身来,做了“和平”与“希望”的简短致辞。30年前,巴伦博伊姆就曾率领以色列爱乐乐团,挑战以色列自1948年起禁止公演德国作曲家瓦格纳作品的不成文规定。20年前,他再次不顾当地政府与集中营幸存者的抗议,在耶路撒冷演出瓦格纳的音乐,引来口诛笔战外加大街上被掷蔬菜的遭遇。但几年前巴伦博伊姆对我说,他已经停止挑战这一“禁忌”:“交响乐团在选拔乐手时,会让他们演绎瓦格纳。我知道,私底下很多人都会听瓦格纳。以色列虚伪得很。”乐界不少人质疑他身为音乐家介入政治的野心,他的行为准绳,大概能够在他与萨义德跨越五年的对话笔记《平行和矛盾: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中找到注脚。
在伦敦,我曾向巴伦博伊姆提问:身为音乐家介入社会政治,他期待能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巴伦博伊姆的回答是:“ 人类一千年前就开始互爱互恨,彼此嫉妒。难道你让我就安坐家里当个搞音乐的吗?那就不叫演绎音乐了,而只是在奏响一系列的符号。音乐不可能为社会、政治服务,可当音乐在不断变成为另一种介质的状态时,它是生命的隐喻。音乐在声音之间、在朝生暮死的事物之间制造联系。当指挥和乐队用同一个‘集体的肺’一齐呼吸之时,它才是音乐 。”
25年前巴伦博伊姆与萨义德共同创办的“西东合集”乐团,名字取自德国诗人歌德晚年以东方题材和诗体表达西方诗人思想的诗集《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van)。除了西东合集乐团,巴伦博伊姆20年前还在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开办了一家针对难民营儿童的“音乐幼儿园”。他认为,在柏林,给孩子上一堂小提琴课,就是对孩子提起对音乐兴趣的一小时;但在巴勒斯坦,则是“远离暴力、远离原教旨主义的一小时”,这之间忽然便别有洞天。巴伦博伊姆又补充说,这并不是说巴以国家对古典音乐特别能产生亲缘感的意思,而是“当你怀着理解将音乐介绍给孩子们,音乐便能丰富他们的生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2016年,巴伦博伊姆在柏林开办“巴伦博伊姆-萨义德学院”(Barenboim–Said Akademie),这所学院如今已是一所受到承认的德国国家级音乐与人文大学。学院的学生不仅学习音乐艺术,还要学习包括欧洲和中东历史、哲学和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以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对话。学成后的部分学生,也成为了西东合集乐团的乐手。
九年前,巴伦博伊姆曾对我说,他心目中最乐观的理想图景是“在适当时机下,中东将成为欧洲与亚洲、欧洲与非洲、西方与东方的完美桥梁”。他引述法国当代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的一句话说:“创造力只在预见不到却变成必要的时候存在”。他认为布列兹“以身示范了这句话,以激进的方式改变了音乐本身以及社会对于音乐的态度:“他一向清楚该激进时需激进,因为那是音乐与社会发展所必要的。但同时,他做事从不武断,而总是保留着不断往前进步的能力。他的前行是建立在对于过去的一种很深的认知之上的。一个真正属于未来的人必须了解过去,对我来说,皮埃尔•布列兹永远是一个先锋的典范。他达到了一种理想的悖论:用头脑去感受,用内心去思考。”
在这晚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内,西东合集乐团再次向我们呈现了音乐可以是冲突之外的桃源。在这场逍遥音乐节的演出上,巴伦博伊姆没有说一句话,事实上,他连来回返场谢幕都显得步态蹒跚。但我们见到散场之前,台上包括巴勒斯坦、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在内的年轻乐手们,都纷纷转身向相邻的乐手张开双臂。一切结束于拥抱之中,
文章编辑: mormonconvert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