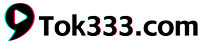责任编辑: mormonconverts.com
在担当了夏季奥运会的城市运动比赛和残奥会开幕式的场地之后,巴黎市中心最大的广场“协和广场”将被顺势改建为机动车免入的步道。奥运赛场和看台拆卸后,巴黎市民和游客从此便能从杜乐丽花园步行到方尖碑。
奥运会结束后,我再访巴黎,居行就集中在协和广场。“协和广场”最初的名字是“路易十五广场”,18世纪中期时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委托设计凡尔赛宫的建筑师安热-雅克•加布里埃尔设计建造,用以展示国王自己的骑马雕像。广场始于法国君主制时代,后来却发展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中心,再演变为共和时期的庆典活动场所。广场边上有两座立面对称的18世纪建筑,一动不动见证过一切。
当时,路易十五还签署下契约,允许出售广场周边的土地,并委托凡尔赛宫的建筑师在广场一侧修建了两座对称的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立面。两年后,立面背后的建筑由另一位建筑师路易-弗朗索瓦•特鲁阿尔完成。30年后,法国贵族克里雍伯爵(Count of Crillon)成为其中一座建筑的主人。广场上当年两座对称的建筑一直保留了下来,不过贵族家已改造为酒店Hôtel de Crillon,只是仍旧保留了“克里雍”家族之名。
这幢楼有时会被称为“爱丽舍宫的前厅”,曾见证和经历两位法国国王的统治、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的兴衰及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的诞生,但最具戏剧色彩之处莫过于与法国末代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联系:王后本人是克里雍贵族家社交圈的常客,还时常来上钢琴课。她上钢琴课的房间正对着协和广场;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在广场上被斩首,“路易十五广场”也被改名为“革命广场”。
出于好奇,我摸到了安托瓦内特当年的钢琴房,房间变成了今天的会议厅“Salon Marie-Antoinette”,不出所料也是以她命名。这个厅挨着的房间,则是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历史时刻: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等各国代表在此会面,并于1919年起草了《国际联盟公约》。“玛丽•安托瓦内特厅”内最抢眼的是一面墙上保存了250多年的奥布松(Aubusson)手工挂毯,然而画中的神话和风景织造细节再丰富,也难与我在踏出阳台、俯瞰协和广场那一刻的脑际运动相比。
多少年来以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人生做文章的文艺作品后浪推前浪,本届巴黎奥运开幕式上哥特式致敬法国大革命的篇章,令人在镜头切换到一身粉红的王后之时重新思考法国人对昔日王朝的复杂感情:君主制早被彻底推翻,君王生活却在现代被反复玩味。
法国人常说,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生活趣味直接影响了巴黎贵族阶层的风尚。有一些风气沿续到了今天,又成了大众社会的趣味。比如一款名为“coupe”的宽口矮脚香槟杯,据说就是以这位法国王后的胸部轮廓为基础而设计出来。又比如,餐厅L'Écrin的桌面会先摆上一个没有底座的香槟酒杯,然后侍应生会迎着客人有点儿不解的目光开始讲故事:“据说,这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设计的香槟杯,没有底座,一放手就会倒下;法国王后以此鼓励大家‘喝香槟,不要停’”。
像这样的一个例子,用以说明18世纪法国社会的高度分化再合适不过。克里雍家的私人宫邸象征了贵族的权力和奢华生活,“让他们喝香槟“的安托瓦内特,完全无视百姓的经济困难。她的奢靡举止激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动荡与不满情绪已积聚到了临界点。当大革命爆发,法国君主与王后被斩首示众,许多贵族的财产被没收,作为贵族象征的私宅有的被改成其他用途,有的遭到大规模破坏。
然而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今天我们坐在昔日克里雍家里,建筑本身彷佛化身为一头会呼吸的生物,年代层次连绵起伏。
巴黎有侵蚀墙石的霉菌,古建每20年要修一次外墙。克里雍家最近的一次装修2013年,那时Hôtel de Crillon已转售给了沙特阿拉伯的一位皇室成员。这次重装持续了四年,新团队进来,决定剥掉1980年代的抛光大理石风格,改为巴黎石灰石搭配柔和的矿物色面料和墙面装饰,按照现代居家的氛围去做布置。巴黎人Roula Noujeim对我说,近年法国大众的口味和国际游客的需求都已改变,如今的旅人,会对两三百年老的博物馆式古建酒店退避三舍,而倾向于住到舒适亲切的环境中。另外,巴黎市民们向来对城府极深的私人宫邸敬而远之,所以,负责重装的室内设计师选择割舍掉华丽的巴洛克装饰和大理石细节,换上平民化的风格,将门槛砍低。即使是米其林一星的法餐厅L'Écrin也丝毫不见传统法餐厅的傲慢姿态,进门客人可以自己选座位,菜单不再刻板,而是由客人在食材清单中剔除自己不喜欢的部分,厨师再为消费者度身定制当晚的菜式。
上月中旬到达巴黎之时,奥运结束后的拆装工程还在进行,酒店工作人员提起就在门前举办的滑板、三人篮球等奥运项目比赛时眉飞色舞。这座立面于1896年被列为法国国家历史文物的古典主义厅堂内,挂满了当代艺术家设计的滑板装置。过去专注于老派法兰西风尚的空间,看得出已为现代及全球化的影响让出了位置。除了室内装饰,这一点也表现在了餐饮上面,比如法餐厅L'Écrin里出现了这样一幕:法国小哥端出2009年云南老树普洱茶和茶具,在饭桌旁洗茶沏茶。又比如楼里新近开了两间由名厨保罗•佩莱(Paul Pairet)主理的小馆。这位厨师虽然是法国人,但他已在上海生活了20年,其在餐饮者的影响力也主要来自他在上海开的三家餐厅,尤其是名为“紫外线”的先锋馆子。法国厨师回归家乡开餐厅,我见到了牛油里加酱油、芝麻酱拌菠菜这些西餐传统中并不存在的做法,但中餐爱好者一看就会心。
正如协和广场早已远离了君临天下的时代,边上16世纪建成的杜乐丽花园,也从原来的法国王室私家花园变成19世纪热气球升空测试和21世纪当代艺术装置的发生地。巴黎市中心这幢旧瓶装新酒的古建筑,如今谁是业主已不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属于公众,属于游客和当地人。一幢法兰西贵族古建的历史变迁、风格变更,一直都在折射社会变化。协和广场需要还路于民,始于养尊处优的贵族家,也必然要在天生的排他性和对大众友善的法则之间,掌控好那架跷跷板。
文章编辑: mormonconverts.com